〈車過嘉南〉林禹瑄|木凱賞析現代詩
作者在三段式的結構中,以一種如歌的行板方式,在車行進間,展演了窗外風景、旅伴互動與內心聲音。就像在詩裡唱歌,作者每段當中都藏了許多迴環反覆的字詞巧思,三大段裡,都有「我們前行」的主題(theme)變體穿插在行文當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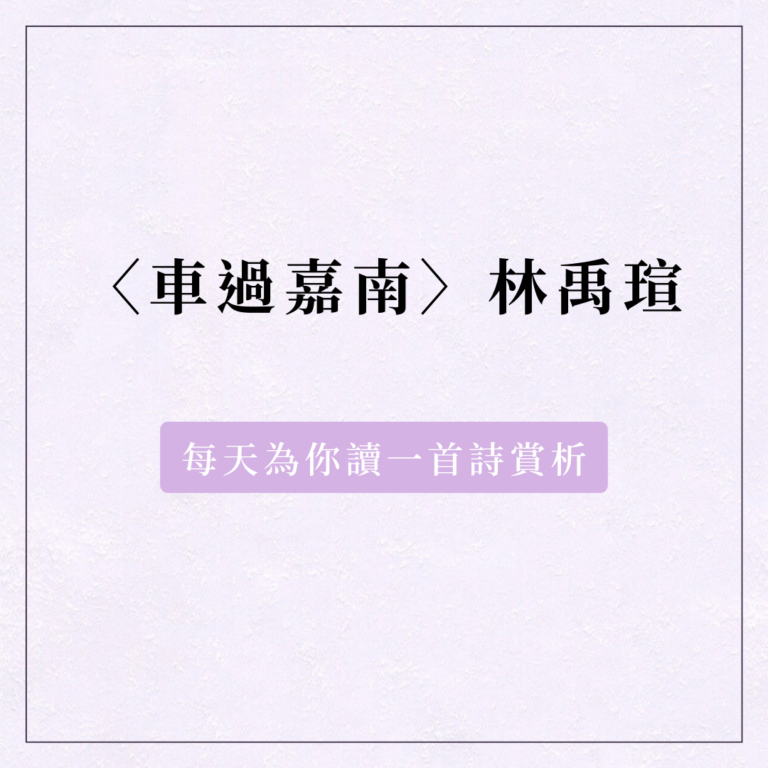
作者在三段式的結構中,以一種如歌的行板方式,在車行進間,展演了窗外風景、旅伴互動與內心聲音。就像在詩裡唱歌,作者每段當中都藏了許多迴環反覆的字詞巧思,三大段裡,都有「我們前行」的主題(theme)變體穿插在行文當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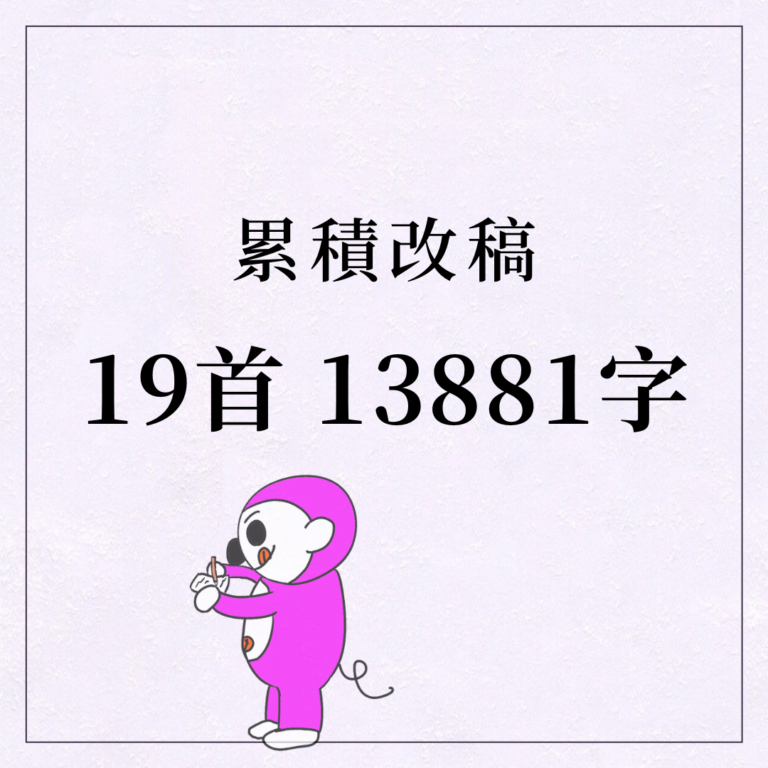
不用搞得很複雜,好像一下要番茄鐘,一下要儀式感。都不用,就是規定自己,在一天的某段時間內,就是坐下來開檔案寫作。
這段時間不能做其他事,不能看書、看影片,不能滑手機、回訊息。
尤其要注意那些,自己一有壓力就會跑去做的事(ex:打掃、翻書、查資料、規劃行程…),這些要有意識的制止自己,暫時別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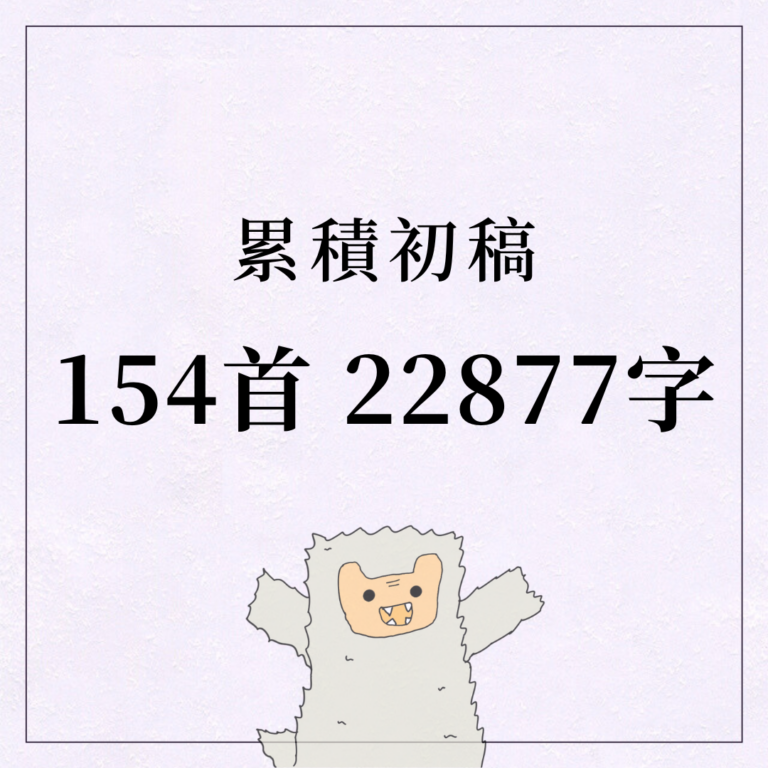
初稿對我來說就是,只要有一瞬的靈感,或是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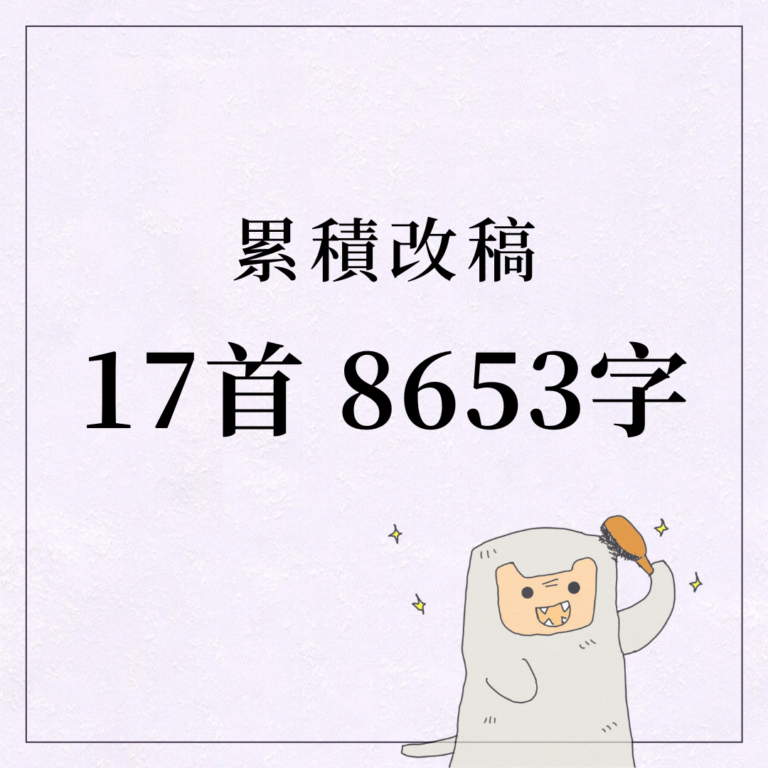
本周幾篇,都會是我重新檢視《城市燈塔》詩…

今年四月中,有幸獲得國藝會創作補助,我的詩集企劃《城市燈塔》,案子預計從2023年5月1日,至2024年4月30日,為期一年的創作。想說機會難得,不如就把我創作這詩集的過程記錄下來吧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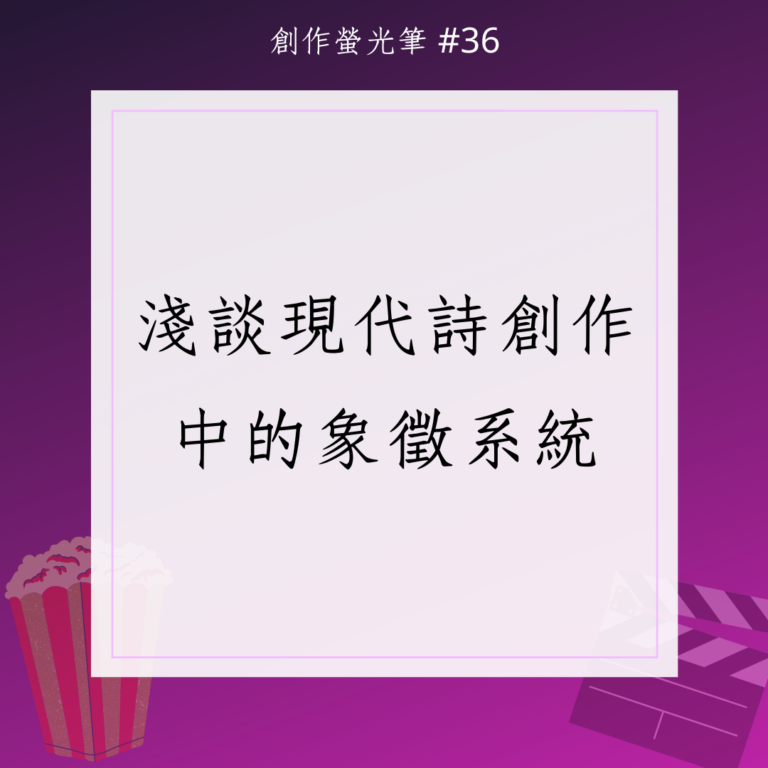
「我們用一個東西去比擬另一個東西,這兩件東西最好距離夠遠,又同時具備平行的相似性,連結的方式要精準有說服力,夠遠則表示有創意。也就是要找到一個夠有創意且執行度高的表現策略。」── 羅智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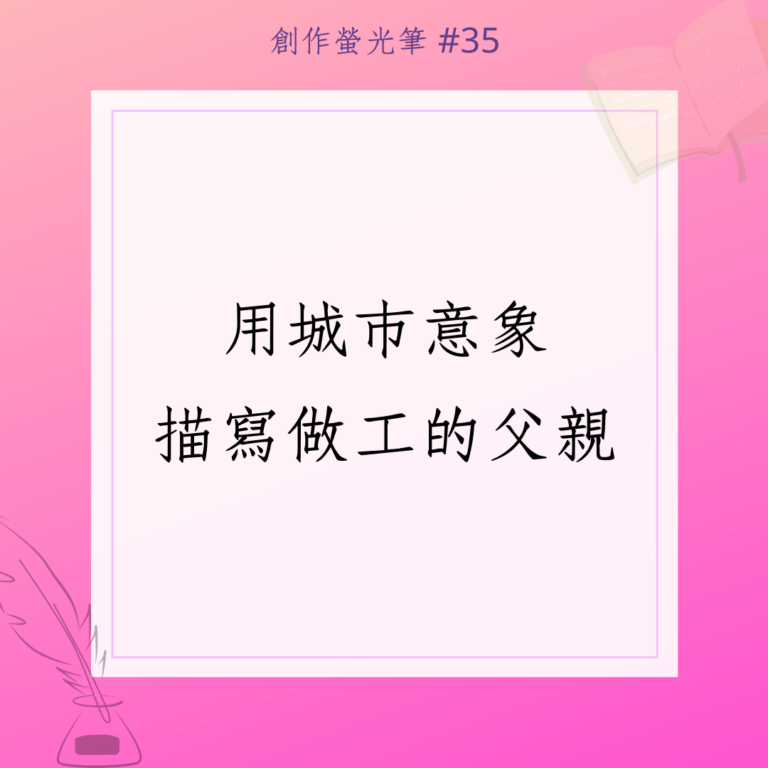
「父親漸漸聽不進我們言語
當他攤開手心,城市街景圖繪沿著他的長文爬行」
──廖筱安〈父親是臺北的戀人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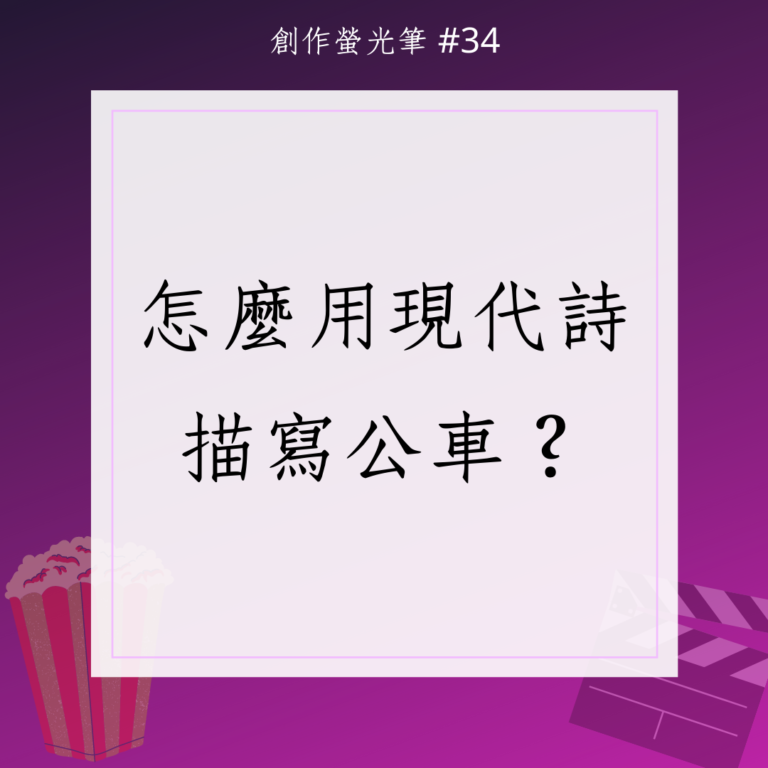
「車燈亮起時
就化作鮟鱇魚穿進城市腹腔。」──王信文〈我們目睹冷鋒進站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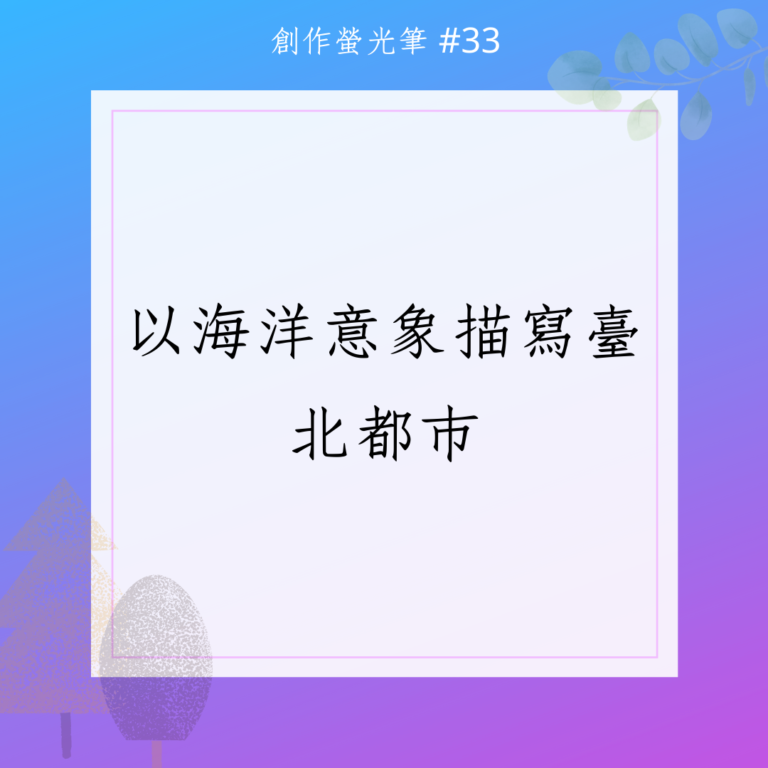
「浪潮轉動一次,便製造無數的私語
海水裡浮現清晰的狼煙,交換慾望的旗語」──李家棟〈假如這裡是海〉